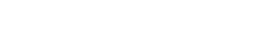汪曾祺的小说“伎俩” ——读《岁寒三友》
2023年10月07日 10:41:09 作者:苏北 来源:2023-10-07 第27,740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·文汇报社出版 审核:
岁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,汪曾祺《岁寒三友》则开宗明义,是指三个人:王瘦吾、陶虎臣、靳彝甫。谓此三人品行高洁也。
像《岁寒三友》这样一万字的小说,得储备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才能写出来?我去年底又读了一遍,在书上做了好多批注,今天再读,仍然惊奇于它的好。汪曾祺的小说究竟要读多少遍,才是个够?
近看到一篇短文,认为一个好的作家,要能够有文学表达的精密度和分寸感。这其实是非常难的,而汪先生正是在此“精密”上,做得最好的作家。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,才那么迷人。
这篇《岁寒三友》的故事,读者自己去看就可以了。我说一点细小的东西。
首先这三个人名:王瘦吾、陶虎臣、靳彝甫。起这三个名字,汪先生是有所考虑的。王瘦吾是个开绒线店小铺子的,人也瘦,肩胛骨在长衫外都看得清楚,为人又忠厚老实,本分而生活清贫。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,他的名字合他的职业。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说“陶虎臣长得很敦实,跟他的名字很相称”。靳彝甫是个画家,不是那种大画家,他画画,也只能糊个口。他清高,生活有雅趣,生活虽半饥半饱,可有滋有味。天井里有花草,用莲子种出荷花,水里养一二分长的小鱼。
——汪曾祺没有一篇小说人物的名字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。如小说《金冬心》里的盐商就叫程雪门,《鉴赏家》里的大画家就叫季匋民,卖果子的就叫叶三,《鸡毛》里的文嫂就叫文嫂,那偷文嫂鸡吃的经济系同学就叫金昌焕,《星期天》里的校长叫赵宗浚,而那个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静仪。还有很多,汪先生的小说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,有兴趣真可以编一份《汪曾祺小说人物表》。总的说,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,但根据人物的身份,也有叫陈泥鳅、李三的。
在这篇小说里,汪先生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尽情地往里面装,包括许多风俗。他实在是个喜欢写风俗的人,而且写得好,可完全融到小说中去,给小说增加了许多生气。在这篇小说里,比如,城镇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场景,绒线店啊,炮仗店啊,小城画师啊。还有各种杂知识,比如关于绘画的(小城的画家和画师们)、民俗的(斗蟋蟀、放炮仗)。反正杂七杂八,汪先生说得都很有兴趣。
其次是小说结构。说结构,还真是没有结构。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实实去写(仿佛极笨拙)。一块一块的,清清楚楚。说完一块,再去说另一块。先介绍王家绒线店、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画店(包括靳彝甫祖传的三块田黄)。再写三人都交了点好运。王家开了草帽厂、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错,靳彝甫斗蟋蟀挣了点小钱,又遇见了季匋民(要买他的田黄,靳说,不到万不得已,是不会卖的,此处为后文埋下伏笔),推荐他办画展,建议他出去见见世面、开阔眼界。
小说一转折,只用了四个字:这三年啊!
王瘦吾的草帽厂的生意被人挤了,陶虎臣炮仗店没了生意,家里断了炊,嫁(卖)了女儿,女儿得了病。正在两家已经活不下去了的时候,靳彝甫回来了。靳彝甫咬牙卖掉了三块田黄,接济两家。这样的交往,当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,也颇具古风,有一种“但使风俗淳”的意味。当然,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。
这样的小说写法,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,正面写到王、陶、靳三人的接触只有三次(一次靳彝甫上门送匾,两次小聚)。因为汪先生说得好,说得有意味,说得深情,读者不费劲就读下去了,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给小说中的人物牵着走,读完还意犹未尽。虽然直接写三个人交接的地方少,但读者又无时不感到他们在交流,无字处皆有字也。
这篇小说实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,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。你可以说是别出心裁。别出心裁的好处是写出了特色,但也颇有难处,还要有识货的人欣赏它。
前不久在高邮,和学者杨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。金是汪先生的妹婿,他一辈子的职业是医生。金先生见到我们,交流了一会儿,他即很认真地询问起一件事来。他对杨早说:
“给您说个事。”
杨早:“您说。”
金:“汪先生的《岁寒三友》能不能拍个电影?他的温暖程度不亚于《茶馆》。”不知道金先生为什么用“温暖”这个词。
金先生接着说,“有一年在北京,大嫂问大哥,陆文夫的《美食家》拍成了电影,你的小说什么时候拍成电影?大哥说,我的小说不好拍。”
这让我想起同是在高邮,见到同样也是汪迷的张国真先生。张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,他非常直接地问先生:“如果改编您的小说拍电影,应该选择哪位导演更合适?”汪先生向烟灰缸里掐灭烟头,戏谑而平静地说:“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。”
想想当年《岁寒三友》发表的经过,已经够费劲的了。还奢谈拍电影。先是汪先生托一个同事带给《十月》杂志(这位同事有个同学在《十月》工作,这位同事还特意骑车送了过去),过了一阵没有消息。汪先生叫他给问问,《十月》的那位同学说,这个小说写的主题是什么?意思是不好发,便退了回来。过一阵,汪先生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的《受戒》有了点影响。《十月》的主编一次到京剧院来,又将稿子要了回去,发在了1981年《十月》的第3期上。想想也真是有意思。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发表的那些小说,早没人议论了,而这篇《岁寒三友》,却多年来不断被人谈起。真是“解人”不易呀!同时也可设想一下,汪先生那时的寂寞和孤独。
在这篇小说中,我也看出一点小小的不足。最后嫁给那个驻军连长的是陶虎臣的女儿。可在小说中只写到王瘦吾的女儿,对陶虎臣的儿女一字未提,最后忽然冒出一个女儿来,有点突兀。总之不太完美。我这点小小意见,如果汪先生能够知道,我想他该会同意的吧?
(本文作者 苏北)